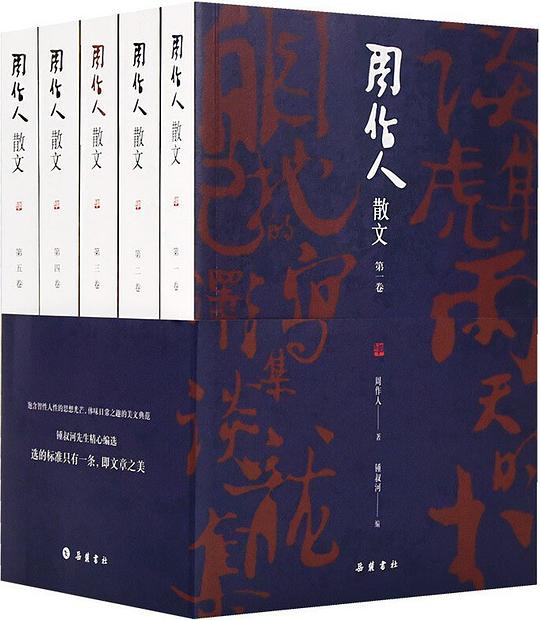
《周作人散文(全五卷)》周作人散文:「文抄公体」的思考
书名:周作人散文(全五卷)
1
0

跑得飞快 2023-08-16 23:09:40
周作人于三十年代初开始写作的散文,被当时人命名为“文抄公体”。赞成者如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中称赞:“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入古雅遒劲的一途。”贬斥不解者如林语堂在《记周氏兄弟》中评价:“然而后来,专抄古书,越抄越冷,不表意见。”实际上,让周作人留名文学史,或者说展现周作人本人风貌特点的,恰恰是周作人创作的系列“文抄公体”散文。
比如乃兄鲁迅后期在《且介亭杂文》等晚期杂文开始的文体实验——将报刊的新闻、时人的言论、查禁的书目、古书的段落并置——从而造成一种针对现实的反讽戏仿揶揄冷嘲的效果,同时也一以贯之地体现鲁迅关怀现实、抨击时弊的风格。
周作人遴选符合自家性格特色的各家文章,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在排比罗列、次序安排、摘句寻章的篇幅上,无时不刻透露出自己的意见。因为在他的价值观念里面,重要的并不是去创造什么,而是发现什么,认识什么。这与钱钟书《谈艺录》,尤其是《管锥编》中表露的观念若合符契,也与由来已久的儒家经学传统“述而不作”大有关联。
世界既然是一个相对恒定的存在,种种重要的经验和常识既然是已给定的,那么人类所要做的工作就只是去发现和认识这些经验与常识,周作人的“抄书体”散文所做的工作,事实上就是对已有发现的再发现,发现世界的本真,然后通过对经验的筛选、转述和评判,进而画出世界的本真。由于周作人眼里的世界是琐碎的、经验性的,那么为了画出一个真实的世界,他的文章也就必然呈现出琐碎、经验性的特色。
系统性宏观架构的论文,看似高屋建瓴,实际上不堪一击,远不如零敲碎打、当头棒喝的片段之语得来的真切,黑格尔常说自己的体系无懈可击,哲学到他这里就宣告终结,在《哲学史讲演录》中对孔子不成体系的论断不屑一顾。如今看来,除了专业研究者,黑格尔那套理论体系鲜有问津,穿越两千年的历史尘埃,仍然熠熠生辉的却是孔子所言的“常识”。
周作人就是要回到这种“片面的深刻”,找到“万物皆备于我”的真知之路。与此同时,三十年代的处境,尤其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也令周作人不得不回到内心,借由文学复古,重建民族形式。如他对传统文人笔记、尺牍、日记的爬梳、摘抄,又受到早年接受章太炎教育的影响,即是对儒家人本主义传统的发掘与建构。周作人在北平时的苦闷心境,使其不得已收敛笔下曾经“浮躁凌厉”“冲淡平和”的文字,放弃启蒙者的呐喊姿态,退隐到后场,成为一个借古人文字,浇心中块垒的沉默者,也渐渐将浮躁凌厉的外露情绪与冲淡平和的内敛气度融合无间,形成讲求真实、淡化感情、注重思想、松散无规矩的独特风格。
要言之,周作人的“文抄公体”、鲁迅的文学史研究、胡适的整理国故等等复古回潮事件,显然不是简单地说一句思想转变那么简单,更不是用斥责其表里不一的蛮横语气得出粗暴结论。因为这些思想家的思想“危机”不是外在的,甚至也不是由外部历史事变决定的,而是内在于启蒙思想运动的现代性逻辑的展开。把他们放置在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中来衡量,局限在激进和保守两个阵营中站队,采取一种非此即彼的态度,是不能很完整地描述出这些中国思想家的全貌及其演变的。
他们的转变不如用“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加以说明。如果嫌理论爬梳太麻烦,简单来说,普遍性即是表明自己与西方的普世价值并无不同,特殊性则是强调自己的民族主义。特殊性不但不是普遍性的对抗力量,相反,普遍性需要特殊性才能展开自身、证实自身。特殊性的追求内在的蕴含于普遍性之中。周作人的搜求古籍版牍、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章太炎由早年革命转向晚年尊孔读经,与其说是传统下的复古,不如说是现代性框架中的全新创造。换言之,西方产生以后,就必然创造一个与西方对应的“中国”。没有作为特殊性范畴的中国、传统的存在,以西方、现代的普遍性诉求根本无法达成。因为中国-
相关推荐
萤火谷的梦想家
艾莉森•麦吉出生于1960年,是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同时也是大都会州立大学创意写作课的教授。她的作品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并出版,也曾被提名普利策奖,并获得苏斯博士奖金奖、克里斯托弗图书奖、美国 [美]艾莉森•麦吉/[美]克里斯托弗•丹尼斯/绘 2023-03-27 16:50:25© 2023-2025 百科书库. All Rights Reser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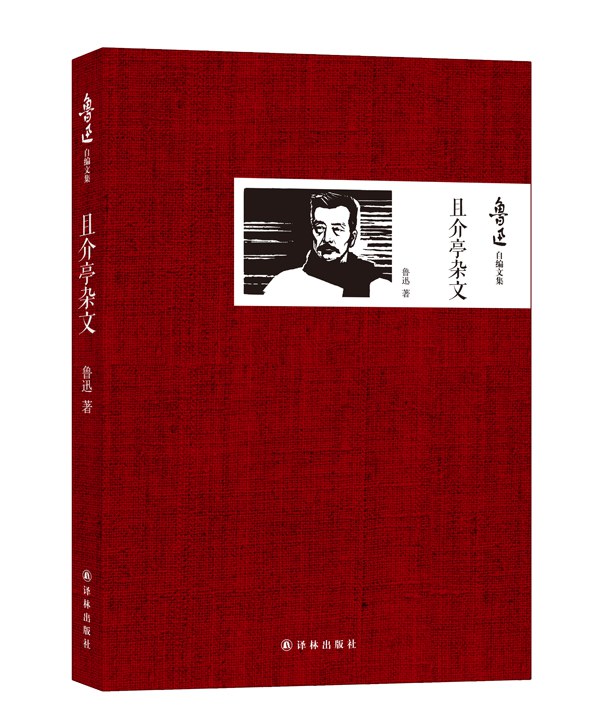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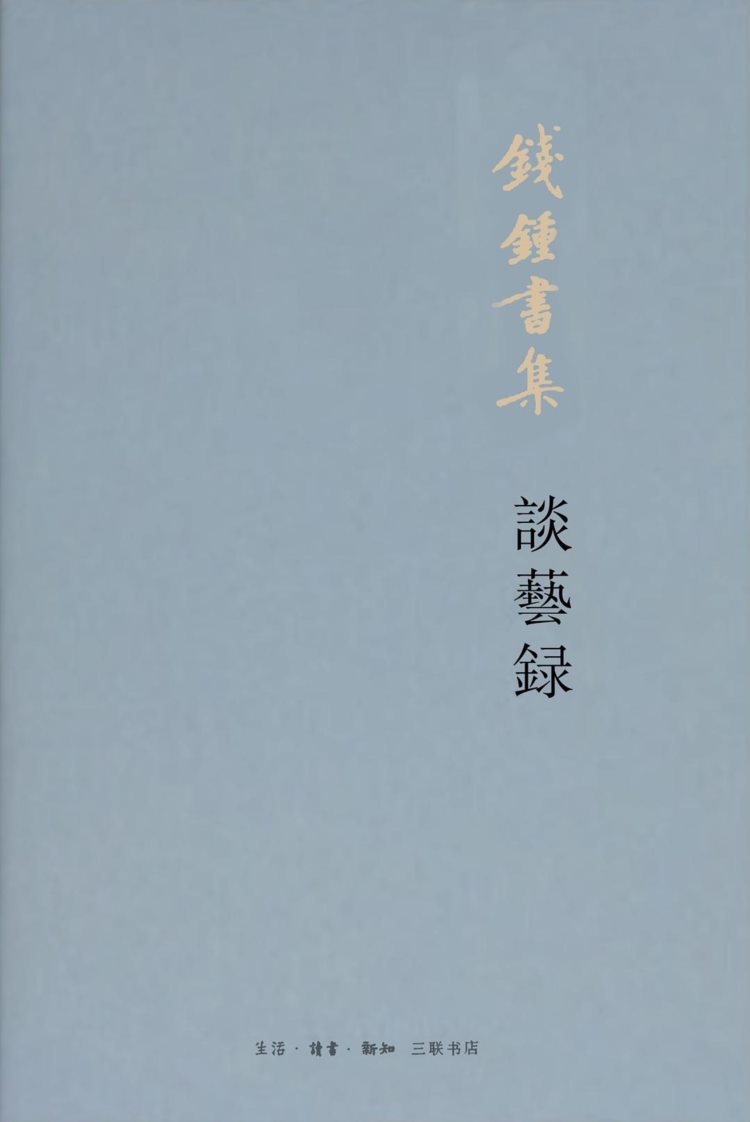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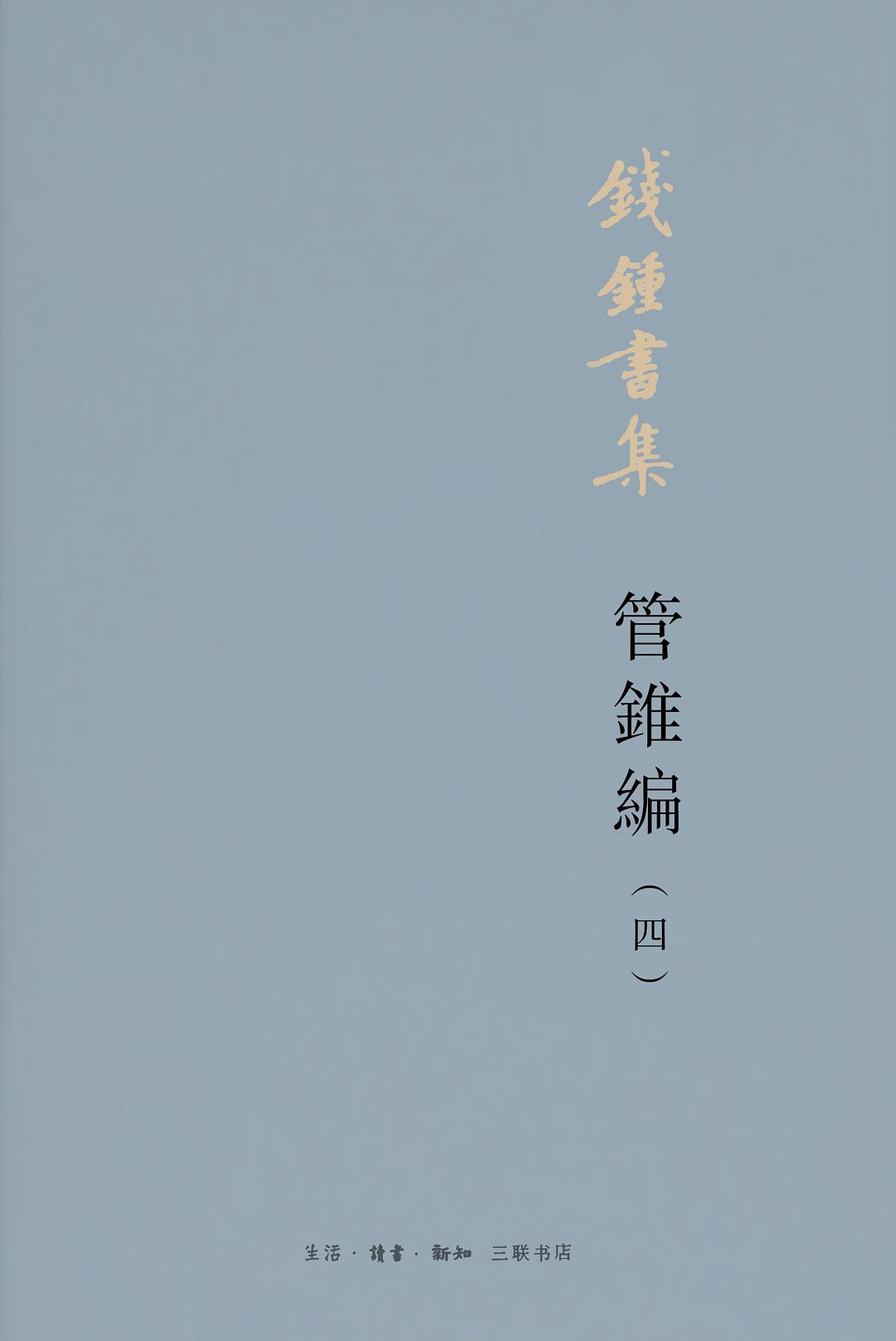







发表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