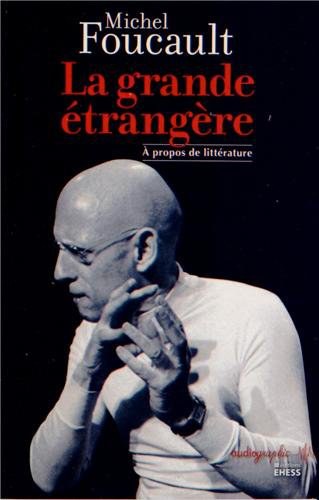
文学之旅:La grande étrangère读什么是文学
1
0

飞天小女警 2023-08-04 05:11:38
原书:pp.75-104
《什么是文学》中提出的核心的“文学—语言—作品”三角,展现了福柯的伟大愿想:不单将文学上升到其早期话语理论中最重要的地位,而更是提出一种别于遵循于大写逻各斯的哲学路径的可能。
首先,诸如《外界思想》、《僭越序言》、《文学与疯狂》、《雷蒙·鲁塞尔》等文本无一例外都可以归入这个三角中(甚至这个三角本身的灵感正是来源于《雷蒙·鲁塞尔》)。
其次,这个三角复杂的关系——其中任何一角的解释必须囿于它与其他两角的关系,而任何一种关系必须囿于关系之外的另一角——直接宣告了本体论的破产。
在《梦与存在》中,福柯围绕梦的主题阐释了一种简单关系,即,通过对辨证法的否定以及经验性的强调,勾勒出一个被称之为“梦的宇宙学”的可同时容纳梦的内在性与超越性的双重性空间。
而在他对阿尔托的阅读中,这一空间漫游至一对既跨越时代构型,也跨越界限与中心的对比——巴洛克疯狂与阿尔托疯狂;空间的双重性也分别被对比的两端所代表。
而比《什么是文学》晚两年出版的《外界思想》则着重强调双重性中内折(replier)向外展(déployer)的单向转化。但无论如何,以上这些作品所针对的都是双重性本身,它们没办法解释为何梦、疯狂、文学、语言甚至福柯所分析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同属其中。
要完成这一解释,福柯就要尽可能地将单一主题中双重性动作扩写至他最开始在梦这一主题中的空间性设想。而这,正是《什么是文学》的任务。
所谓“文学—语言—作品”三角,指的是文学语言作品这三个顶点以及即语词的厚度;文学,即文学本身的虚无;语言,即赫拉克利特式的保证能够理解的最低限度,一切低语,一个透明的系统。
然而一旦我们追问任何一个顶点的本质,最终都会在一种误导与拒绝的张力中无功而返。在《现象学经验——巴塔耶经验》中,这种无功而返是与现象学原初被给予(Urgegebene)相对的可能的可能性、无法到达的终点、“lêtredelimpossible(福柯在此并没有将“impossible”名词化)dêtre”。
而在《什么是文学》中,无功而返是对文学”顶点的寻问,是对上一种无功而返的空间性堆叠。询问“文学是什么”,首先牵涉到的是文学与语言以及文学与作品的关系。在“文学—语言”中,文学是“fable”,之所以不翻译为“寓言”,是因为福柯在“ineffable”至“fable”的语词滑移中,恢复了“fable”的原本意思:人群中的低语、交谈,或是熟悉的、私人的、个人的对话。
文学只有作为语言内部被挖空的距离,作为语言无意义的低语,并如同在《外界思想》“我说话,我说谎”中所演示的“言说的及物性被榨干”时,我们才可以说,某种意义上,文学是一种如同文学的“在其原地摇摆不定的语言”。
其次是文学与作品的关系,一言蔽之,便是只有作品的厚度被压缩到如同文学的白纸的厚度时,只有每一个字词都定格在落笔瞬间时,我们才可以说,某种意义上,文学是一种如同文学的连续性,一使得作为其碎块的作品存在的连续性。
然而至此我们所得到的都只是两种“如同文学的东西”,因为这两个关系本身受限于它的外界。比如,谈论“文学—语言”,就得正视“文学与语言的关系受限于作品的静止、绝对不变的厚度中”这一事实;谈论“文学—作品”,就得正视这一关系也会受限于低语的语言这一事实。
因此,若继续追问文学是什么,最终等待着我们的只有两种文学形象:要么进入拟像的(simulacre)空间,要么被僭越所否定。
作为文学与语言关系的“外界”,作品将喜欢刨根问底的我们带入福柯所说的“图书馆的反复言说(leressassementdelabibliothèque)”中,其中,所有语词都朝向文学,呼唤文学。作品停留在想成为一本书的厚度中,力求加入某种文学的坚实存在。
在这个意义上,它是既指其内容,也指某种“文学之所是(cequestlalittérature)”的一分为二的统一体
相关推荐
萤火谷的梦想家
艾莉森•麦吉出生于1960年,是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同时也是大都会州立大学创意写作课的教授。她的作品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并出版,也曾被提名普利策奖,并获得苏斯博士奖金奖、克里斯托弗图书奖、美国 [美]艾莉森•麦吉/[美]克里斯托弗•丹尼斯/绘 2023-03-27 16:50:25鬼马女神捕1·绝密卧底(上)
腹黑凤凰vs毒舌鸡妖——蓝翎:“小姬,跟我去人界吧!”姬十四:“干吗?让人宰了我做小鸡炖蘑菇吗?”蓝翎:“不啊,让妖怪宰了你做小鸡炖蘑菇更气派。”凤凰蓝翎和鸡妖姬十四生活在无忧无虑的灵界。他们的故乡叫 郝天晓 2023-04-17 00:22:47© 2023-2025 百科书库. All Rights Reserved.












发表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