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倦怠社会:虚假自由和功绩主导
书名:倦怠社会
1
0

好好先生 2023-07-16 23:56:34
韩炳哲没有构建自己的理论框架,而是一直在进行社会分析。他认为,我们经历了从规训社会到功绩社会的转变。在功绩社会中,我们既是主人又是奴隶,这种合一让我们自我剥削。来源于资本主义对效率的要求,功绩社会成为新的社会形态。
然而,韩炳哲并没有详细分析功绩社会/主体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为什么“我能够”变得天然合法并深深根植于我们心中。汪民安在一次采访中表示,绩效也来自他者,如公司的绩效控制、企业文化和精神。然而,即使还存在他者,它们也是隐匿的。例如,我身边的孩子们不需要家长或学校强迫,就会过度投入学习中。这种自我剥削似乎是一种自我认同,而不是来自他者的要求。因此,我更倾向于将这种“我能够”的绩效精神视为一种意识形态,通过教育和宣传根植于人们的内心。然而,这种推论可能过于浅薄,无法解释所有现象,让人不满意。
在《空无与行动》中,描述了法国心理学家让-莱昂·博瓦的一个心理实验。他让受试者分为两组,实验中包含让人不愉快甚至违反道德的内容。其中一组告知可以自由选择退出,另一组则不告知。两组最终坚持下来的人数比例一样,但未告知可以自由退出的人感觉被迫继续参加,而告知可自由退出的人则认为参加是自己的选择,而非外在强迫。他们甚至为不适的实验内容寻找原因,来合理化它们。
实验条件都是相同的,不愉快的实验都来自外在强加,除了被告知是否可以自由退出这一条件。然而,这一条件却让受试者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差异。这个实验的洞见说明了“自由”的巨大心理暗示效应,也能解释功绩社会/主体的形成。当我们被告知是自由的时候,他者的压迫并没有消失。然而,随着对压迫的忍受,我们会内化这种压迫,创造一种虚假的自由来回避对他者压迫的排斥,从而进一步自我剥削。这种变化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进一步深化的必然结果。
以孩子学习为例,教育上要求综合素质教育而不是分数排名。孩子好像有了更多自由选择,但实际上,分数排名并没有消失,而是隐匿在各种环节中(甚至学习目的仍然是高考)。孩子们仍然选择分数竞争,但这种选择成了一种自愿,孩子们构建出一种虚假自由来应对排斥,以实现疯狂的自我剥削。
另一个例子是工作中不打卡、自己合理安排时间的所谓的“互联网精神”。然而,绩效导向仍然存在。虽然员工似乎有更多自由安排工作时间,但内心仍然觉得可以多做一点来提升绩效,最终导致加班泛滥。这种心理让加班被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怨气没有向外发泄,而是全部内化。
因此,“自由”这个高尚的词汇看起来是“天授”的,是与生俱来的。然而,它也容易被当作工具或被误用。齐泽克区分了“形式自由”和“实质自由”。前者是在现有权力结构下给定的选项中自由选择,后者则是改变现有权力结构给定的选项。真正的自由能够反作用于现有规则,增加选项,甚至改变规则。这也说明了西方的自由民主有时是虚伪的,因为在其秩序之外的选择是非法的、不被允许的,甚至是必须消灭的。
与自由相关的功绩主体的“我能够”似乎是天然合理的。然而,我们需要思考一下,我们是否真正具有选择超越绩效的自由去追求新的生活和工作目标。显然,功绩社会没有给予我们这种自由的选择,它让我们认为,我们的失败源自自身不够努力,而不是外部规则。要打破这种循环可能很困难,但我们最终需要认清自己所谓的“自由”的本质。
相关推荐
萤火谷的梦想家
艾莉森•麦吉出生于1960年,是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同时也是大都会州立大学创意写作课的教授。她的作品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并出版,也曾被提名普利策奖,并获得苏斯博士奖金奖、克里斯托弗图书奖、美国 [美]艾莉森•麦吉/[美]克里斯托弗•丹尼斯/绘 2023-03-27 16:50:25鬼马女神捕1·绝密卧底(上)
腹黑凤凰vs毒舌鸡妖——蓝翎:“小姬,跟我去人界吧!”姬十四:“干吗?让人宰了我做小鸡炖蘑菇吗?”蓝翎:“不啊,让妖怪宰了你做小鸡炖蘑菇更气派。”凤凰蓝翎和鸡妖姬十四生活在无忧无虑的灵界。他们的故乡叫 郝天晓 2023-04-17 00:22:47© 2023-2025 百科书库. All Rights Reser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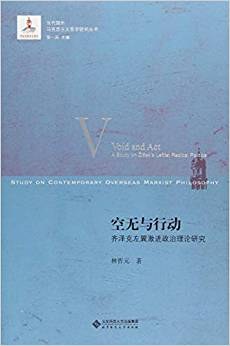









发表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