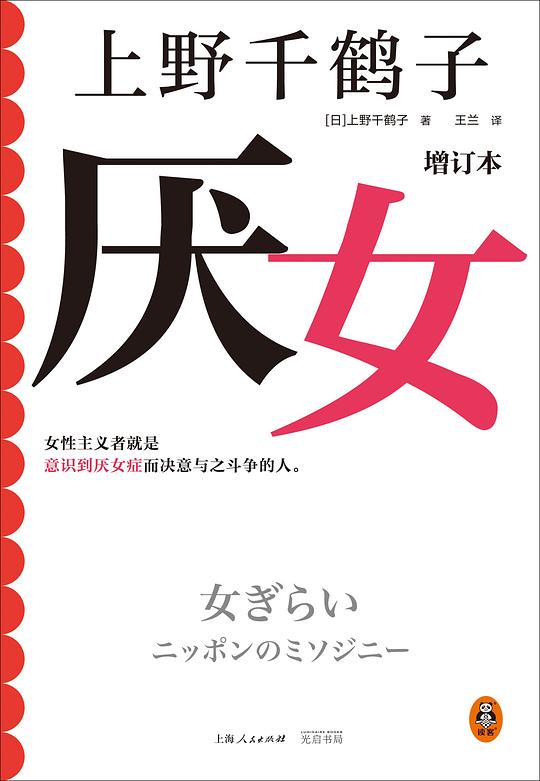
上野千鹤子的“厌女”与列维纳斯的“他者”之比较
书名:厌女
1
0

狂野之心 2023-05-17 10:29:18
这本书我还没读,只是看到原文摘录里有这么一段:
厌女症就是绝不将女人视为与自己同等的性的主体,而是将女人客体化他者化,更直接地说,就是歧视、蔑视。
这是上野千鹤子对他者的定义、理解。这让我马上联想到列维纳斯在《时间与他者》中用“面对面”的共在批判取代海德格尔的“肩并肩”的共在。
社会性在海德格尔那里是在孤单的主体中被发现的,像是荒岛上的鲁滨逊。而列维纳斯与上野千鹤子一样,也将他者理解为女性,社会性在列维纳斯这里是随时有他者的介入打断自我的孤单形成的,最起码也是伊甸园里的亚当和夏娃,不是只有孤零零的亚当。
海德格尔的共在当然不是只有鲁滨逊没有星期五没有他者,但海德格尔的主体与他者是围绕一个共通甚至共同之物建立起来的,即“在其本身形式中解蔽的真理”,此在是无性别的、普适的主体,因此这种肩并肩的共在中,他者并不真正将他者理解为女性,坚持不损害他者之他异性关系。但对这种他者之他异性关系,上野千鹤子的态度却与列维纳斯截然相反,上野千鹤子认为这种有分别心(不知道怎么描述,姑且借佛学术语一用),有性别,是歧视、蔑视,上野千鹤子的理想似乎是在要求海德格尔或费希特的无性别的、普适的此在,不知道是不是该把这种理想称为男女平权或者弗洛伊德的阴茎嫉妒症。从她的态度我只能推测她的理想是这样。
列维纳斯对他者的定义是将来性和神秘性,不可完全被主体所把捉,这让列维纳斯的他者与费希特的非我区别开来。可以说列维纳斯是跟梅亚苏一样的实在论者。因为列维纳斯给了他者这种本体论地位,在将他者理解为女性的时候,主体与女性的相爱,也不呈现为一种融合,而是融合的不可能:爱之哀婉是在存在者之无法逾越的二元性中构成的。它是与一种永远在避开之物的关系。作为他者的他者在这里并不是一个客体,这一客体会变成我们的,或变成我们;相反,它撤回到了它的神秘中。
列维纳斯的他者本体论概念保证了女性不可能被客体化,这与上野千鹤子截然相反。上野千鹤子认为存在者之无法逾越的二元性就相当于将女性客体化,就是歧视、蔑视,就是厌女。
列维纳斯说了自己讨论的不是社会学和人类学,而是本体论。但从他的描述来看,我认为可以将列维纳斯的态度概括为:我爱你不是因为你是谁,而是因为跟你在一起时我可以是谁。我爱你不是因为你是一个完美的人,而是因为跟你在一起时我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因为我爱你,所以我愿意不断的改变自己,也愿意接受你所爱的一切。他所描述的是男性在长择女性又没追到手时候的状态。我认为应该注意对于他者的概念,列维纳斯与上野千鹤子在概念上的绝对预设就有重要的不同。
剩下的等读完了再写吧。
相关推荐
萤火谷的梦想家
艾莉森•麦吉出生于1960年,是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同时也是大都会州立大学创意写作课的教授。她的作品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并出版,也曾被提名普利策奖,并获得苏斯博士奖金奖、克里斯托弗图书奖、美国 [美]艾莉森•麦吉/[美]克里斯托弗•丹尼斯/绘 2023-03-27 16:50:25鬼马女神捕1·绝密卧底(上)
腹黑凤凰vs毒舌鸡妖——蓝翎:“小姬,跟我去人界吧!”姬十四:“干吗?让人宰了我做小鸡炖蘑菇吗?”蓝翎:“不啊,让妖怪宰了你做小鸡炖蘑菇更气派。”凤凰蓝翎和鸡妖姬十四生活在无忧无虑的灵界。他们的故乡叫 郝天晓 2023-04-17 00:22:47© 2023-2025 百科书库. All Rights Reserved.












发表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