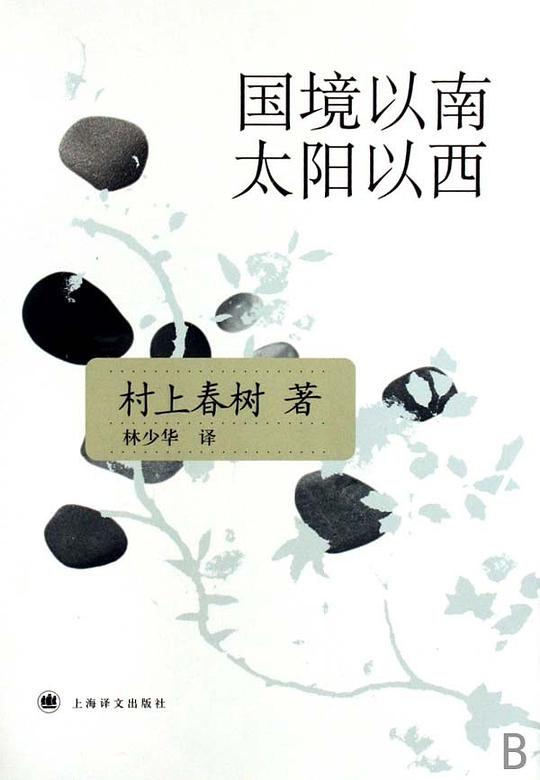
《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南国余晖长存
书名: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
1
0

恒大冰泉 2023-04-23 00:21:16
德里达提出的“延异”为后现代人们的普遍焦虑提供了概括:意义永远是相互关联的,却不是可以自我完成的。从这个层面上看,生命处于这种意义的推迟中,其焦虑与痛苦也根本发源于此。村上这部小说为我们揭示的也是这样一种状态:初在于诸多女性角色的迂回中呈现出愈发空虚的表象,而其心中无法割舍的始终是初恋岛本。
从本书的第六章初遇到一位患有腿疾的女性开始,读者已隐约可以感受到主人公身上这种迂回的根源所在:岛本无处不在,同时又难以接近。到小说的第八章初与她重逢以后,岛本对读者来说看似变得具象了,实则蒙上了更深一层的迷雾:行踪不定的岛本有一段不为主人公和读者所知的过去,如同凭空消失般的岁月。尽管她即在眼前,与初交换着话语、目光甚至体温与其他,以至于初愿意为她放弃现在所有的一切,那种深层的距离感却能使人陷入更大的痛苦,这种痛苦在岛本消失的瞬间陡然爆发。从这里开始,读者便可感受到这样一个事实:岛本似乎不再仅仅而更像一个幻影,一个时来时去的梦,永远无法抓住的意义。
主人公初这个名字所代表的意义也即“初”,在生命这团混沌无序的物质中游走,试图抓住那种原初的渴望。这种渴望来自于意义的缺失,岛本在这里显然就是意义的代名词。
村上在这里采用的手法,尽管已是老生常谈,却仍是值得重提的:一种极大限度使读者接近叙事者的笔调;初的视角即读者的视角,于是在整个故事中,悬念到最后还是悬念,叙事不会向读者揭示任何真相,一如生活向我们展示的东西一样:一种体验性的阅读。那些在我们视野之外的真实、不可知本身构成了体验的乐趣所在。也是因这种体验感我们得以洞见小说所要表达的那种延异主题。
习惯于阅读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读者或许难以适应这种碎片化的、断层的叙事,更有甚者会认为此种叙事消减了主角以外人物的塑造。这种批评与对这种批评的反驳却也是老生常谈了,顺手我们也可以谈谈小说对几位女性人物的塑造。
岛本身上所具有的最大特点便是不可知感,这种不可知感来自于其故事的断层,她的首次出场几乎只以寥寥几笔带过,而随后仅以回忆式的碎片的絮语散落在叙事中间,再次登场已是多年以后,文中有一段对话解释了这场久别的原因:他们虽渴望见到彼此,却都很害怕,害怕年轻时的失望与拒绝。对于断层中的岛本的经历仅以一句话即可概括:她有过一个早夭的孩子;余下的细节要读者想象以自动补全。毋庸置疑地,这会是一个不幸的故事,才会导致岛本对初说的“谢谢你能接纳我”以及在小说后半部分的时来时去,犹豫和离开。至于这个断层中发生的故事本身,在此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那是读者凭借寥寥几个线索完全可以想象的,加以补全只会破坏其体验性;在小说中,人物形象有时无需依靠说过的东西托出,而可在不言中展示。
有纪子作为初的妻,其身上也有一种不可知感,在于岳丈只言片语中透露给初的有关有纪子的过去的一个线索;然而与岛本不同的是,这一线索根本上无头无尾,没有任何得以被读者的想象补充的可能。这并不意味着这一细节的无机,相反,它恰恰需要是悬浮的,正因这种悬浮性,在小说临近末尾初的苦苦挣扎中她才能显示出把初引领回现实强大力量。可以说有纪子的人物形象是在已有的文本中,借助递进式的、生活化的描写突然被树立起来的:她是现实之温柔的化身。
同诸多现代小说中展现的那样,肉欲的议题在这里是暧昧的,它以一种即缠绕又疏离的状态环绕于初的渴望中,时而可以作为意义的隐喻,时而与意义截然分离。在泉那里,初的肉欲
相关推荐
萤火谷的梦想家
艾莉森•麦吉出生于1960年,是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同时也是大都会州立大学创意写作课的教授。她的作品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并出版,也曾被提名普利策奖,并获得苏斯博士奖金奖、克里斯托弗图书奖、美国 [美]艾莉森•麦吉/[美]克里斯托弗•丹尼斯/绘 2023-03-27 16:50:25鬼马女神捕1·绝密卧底(上)
腹黑凤凰vs毒舌鸡妖——蓝翎:“小姬,跟我去人界吧!”姬十四:“干吗?让人宰了我做小鸡炖蘑菇吗?”蓝翎:“不啊,让妖怪宰了你做小鸡炖蘑菇更气派。”凤凰蓝翎和鸡妖姬十四生活在无忧无虑的灵界。他们的故乡叫 郝天晓 2023-04-17 00:22:47© 2023-2025 百科书库. All Rights Reserved.












发表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