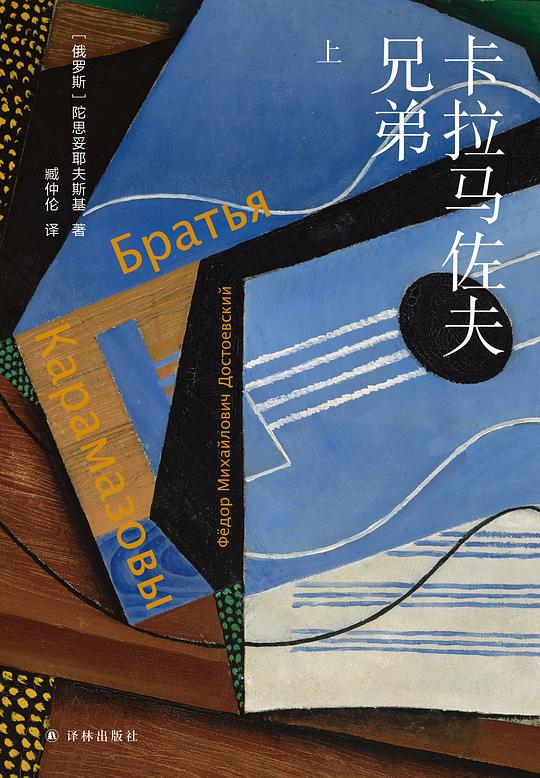
卡拉马佐夫兄弟人物两极化
书名:卡拉马佐夫兄弟
1
0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2023-05-16 13:23:17
记得自己讲过,托尔斯泰对他塑造的人物充满着爱和怜悯,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拢着袖子,冷眼旁观着自己塑造的人物,他喜欢用第三者的“我”站在一旁几乎不带感情地稍加指点(鲁迅的作品里也经常用这种“我”的视角,比如《阿Q正传》),就算有感情出没,那也是前后牴牾着。这种牴牾,尤其表现在对人物的刻画上,即人物的两极化——正与负集于一身。如果读过一些老陀的著作,那细数一下,数数在他的著作里有多少非黑即白的人物,梅诗金和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可以算,前者白的发痴、后者黑的入魔,但论纯度还不及《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阿廖沙,这是我读老陀作品至今读到的最有圣人腔调的完美人物,现实中这样的人恐怕很稀有,绝大多数人都是正负两极都兼而有之,也正因为都有,人就生动起来,有能量输出,单极化的人物很教条、很单薄,所以每当读到阿廖沙的出场,仙气飘飘,实在叫人看着美好,仅仅美好。遗憾的是,老陀没有完成后面的一部就驾鹤西去,否则再读读阿廖沙的成长和养成,从小到老,他能不能坚守着一直的坚守?也是非常吸引人,说不定能成为一部更伟大的作品,遗憾。
其实在阿廖沙与科利亚见面交谈时,阿廖沙就已经从浪漫主义的神坛走了下来,走向了现实。他对科利亚在意被人说可笑时,就努力开导他:“在意自己的可笑,如同魔鬼化成的自尊心,钻进人身上,是魔鬼在作祟”,进一步告诉科利亚要做自己,“现在的人不认为有自责的必要。你要做个也所有人不一样的人;哪怕就你一个人和大家不一样,也要坚持下去,不一样就不一样”。这些言语非常口语化,放在一个品格磊落的人身上,这些话就是强心剂,会叫人更磊落;相反,放在猥琐的人身上,就是催化剂,会更厚颜无耻与自私自利。这就是两极化的一种典型,也是我的过度解读,可千百年来,何尝不是这样呢?阿廖沙的师父——佐西马神父,这么高尚的一个人,死去后在他身上既没看到神迹出现,反而他的尸臭却开始蔓延,臭不可闻,圣人应该是异香扑鼻的。
再看看卡拉马佐夫家那位混账到老的老头子,简直就是一坨渣渣,老渣男一颗嘛,自私、刻薄、吝啬、放荡、好色……抢儿子们应得的母亲遗产、抢大儿子的情人,亵渎神灵、玩世不恭,啥都要就脸不要,典型的陀氏作品里的反面人物,比之前几部作品里的反面人物更叫人厌恶,这个恶人的形象在文字里呼之欲出,人人想除之,最后法庭判定其是死于大儿子之手。可这个十恶不赦之徒也难得会闪现一点人性出来,比如对待家里的老用人,像会良心发现一样,稀罕的表现出父子情,尤其对小儿子阿廖沙。
这本书里登场的人物很多,一个个打量,都是平常人物,有着七情六欲,放荡女会忠贞、忠贞女会恶毒,公诉人会才华横溢,同时自以为是,辩护人会自以为是,同时才情洋溢,甚至到一个房东、车夫、用人、学童、外国人……等等,身上矛盾的两极化无时不在,这种共性是陀氏作品的显示标志。正如圣经里那句话,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墓志铭:“一粒麦子落在地里如若不死,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会结出许多子粒来。”不死、死,一粒、许多子粒,不正是正与负的两极化通过宗教的终极展现么?
这部名著有三块花了好多页的笔墨:阿廖沙与大哥米佳的交谈,米佳长篇累牍般一顿输出;二哥伊万与自己幻像间的交谈,如垂死之人的澹妄;公诉人与辩护人的两段讼辩,现场的看客被他们左右,读者也会被左右。其实读完后,我还是迷惑着,到底米佳有没有罪?弑父的真是他?从某种角度讲,这部《卡拉马佐夫兄弟》和《罪与罚》一样,推理元素很多,尤其是法庭上辩诉双方的唇枪舌剑,再加个陪审团,我怀疑港剧的法庭辩论,老陀是开山鼻祖,但绝不是仅推理小说,不好读,尤其对于没耐心或者阅历不够的人来讲,如果要读,感兴趣,我个人推荐译林的中译版,臧仲伦翻译,译文比较丝滑。
下面抄录一段,体会一下译文的节奏和韵律:
……现世界标榜自由,尤其在最近,可是在他们的这个自由里,我们又看到了什么呢:只有奴役和自杀!因为现今世界说:“你有需要,就应当充分满足这需要,因为你同那些豪门巨富一样具有同等的权利。不要害怕使这些需要得到满足,甚至应当使这些需要日益增长。”……这种使需要日益增长的权利会产生什么结果呢?富人中会产生彼此隔绝和精神自杀,穷人则会产生嫉妒和凶杀,因为给了权利,却没有指出充分满足这些需要的手段。
相关推荐
卡拉马佐夫兄弟
这本书是俄国文学大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之一。故事描述了老卡拉马佐夫和他的三个儿子因为财产遗产而发生的尖锐冲突。老卡拉马佐夫贪婪好色,不公平地分配财产,并且与儿子们争夺同一个女人的爱。一个黑夜,长子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2023-03-22 00:53:56罪与罚
《罪与罚》是一部优秀的社会心理小说,代表着陀思妥耶夫斯基成熟的艺术风格,并使其在世界文坛获得了较高声誉。故事讲述了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在追求拿破仑式人物的过程中,因生活所迫杀死房东及其无辜的妹妹,最终 [俄]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2023-03-31 09:47:26萤火谷的梦想家
艾莉森•麦吉出生于1960年,是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同时也是大都会州立大学创意写作课的教授。她的作品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并出版,也曾被提名普利策奖,并获得苏斯博士奖金奖、克里斯托弗图书奖、美国 [美]艾莉森•麦吉/[美]克里斯托弗•丹尼斯/绘 2023-03-27 16:50:25© 2023-2025 百科书库. All Rights Reser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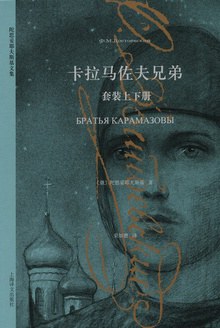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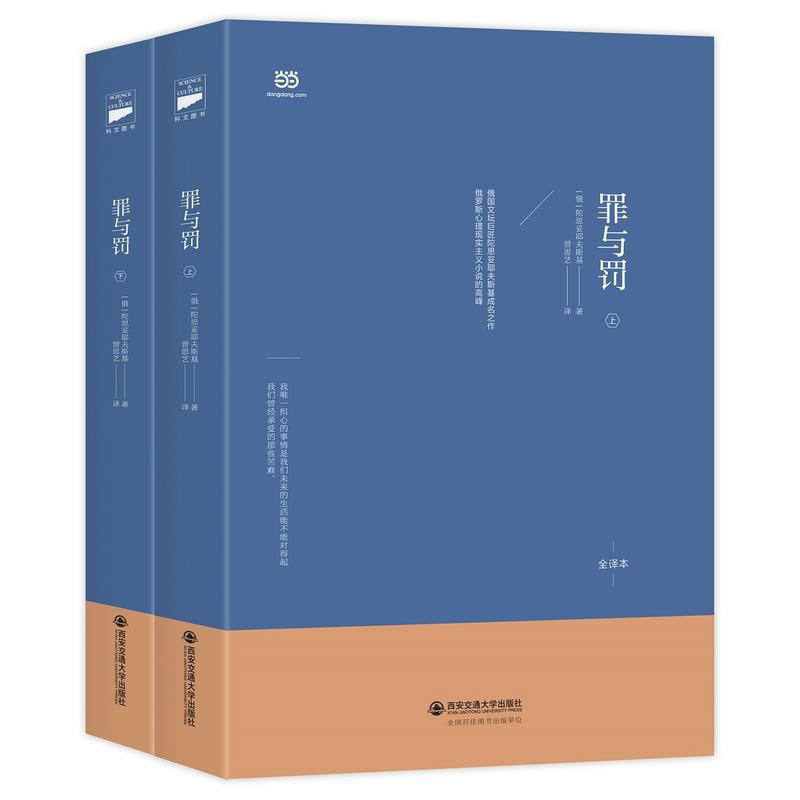







发表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