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书纪年》早于《史记》,司马迁编的《史记》为何与《竹书纪年》大相径庭?
网友回答
题主看法欠妥,有抑《纪年》而非议《史记》之意。《竹书纪年》早于《史记》,就应该以《竹书纪年》为准吗?恐怕未必。
首先,世上本就没有《竹书纪年》传本,拿什么去跟《史记》比较呢?进入宋朝,已很少有人见到《竹书纪年》了,它在那时已亡失了。后来,有人掇拾《纪年》佚文,凑合史传的记事,抄录《宋书符瑞志》的文章,托名梁沈约注,是为《今本竹书纪年》。至清钱大昕、纪均、洪颐煊、郝懿行等已疑其为伪书。朱右曾更力斥其不足信,并从各传世文献中辑出《古本竹书纪年》,1917年王国维加以补充订正,后经我国文献整理专家范祥雍先生校理、订补,加上范先生依《史记年表》整理出的《战国年表》,仅百余页的小册子。可以说内容极为有限,不及《三家注史记》内容四十分之一,怎么能跟《史记》媲美呢?
其次,两书性质各异,《史记》上起五帝下迄汉武帝,包罗万象,是司马迁对其所能见到的文字材料和口述历史的系统梳理,是一个浩大工程,倾注了司马氏几代人的心血和这位伟大史家的真知灼见;《纪年》仅魏、晋史书,迄于魏襄王,仅国别史,而且内容多已残缺,难窥全貌,甚至绝大部分内容需借助《史记》方可理出头绪。
历史学是个材料科学,《史记》以今世逻辑观之,确有不乏推敲之处。但从《史记》记述,与其所运用的《世本》《国语》《左传》《战国策》传本比较来看,司马迁极为忠实文献,并作出了极为精准的把握,这是一个真正史家的可贵品质。但一些列传比较有文学性,博采途说,我们应以《本纪》《世家》《书》《表》为准。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很多考古材料,太史公没法见着,比如长沙马王堆所出十几篇苏秦书信,那是苏门弟子的绝密,所以今天看来,《苏秦列传》有很多不实之处。但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在不掌握《战国纵横家书》的情况下,能作出很多精彩评述,已足见司马迁的睿智。
最后,《竹书纪年》虽系战国中后期史书,但却出土于晋武帝咸宁五年,那时太史公已逝数百年矣。但说实话,数车竹简虽由当时最著名的学者荀勗、和嶠、束皙、卫恒等整理,但时人毕竟已不怎么懂战国文字。若太史公能见着那些竹简,《史记》面貌又当如何,我不敢设想。起码临不着后人说三道四。
没有《史记》,中国文化是什么面目,我也不敢设想。两千年中,《史记》塑造着中华国民精神,太史公可谓不朽矣。我们站在文化巨人的肩膀上,不应该苛求前贤;但像《汲冢竹书》那样的文献,应该越多越好——这恐怕正是史学真正的魅力之所在!

幻想小镇 2023-05-01 23:36:29
1
0
相关推荐
逆天的冒险
我们是天生的冒险家,对冒险的爱从不会离开我们,直到我们迈入垂老之年。”博莱索写道。他认为,“胆小的老头子,在他们的兴趣当中,冒险应该是绝灭了的。”这也是为什么诗人们偏爱冒险,而法律通常是老年人制定的原 (南非)威廉·博莱索 2023-04-10 05:12:26© 2023-2025 百科书库. All Rights Reser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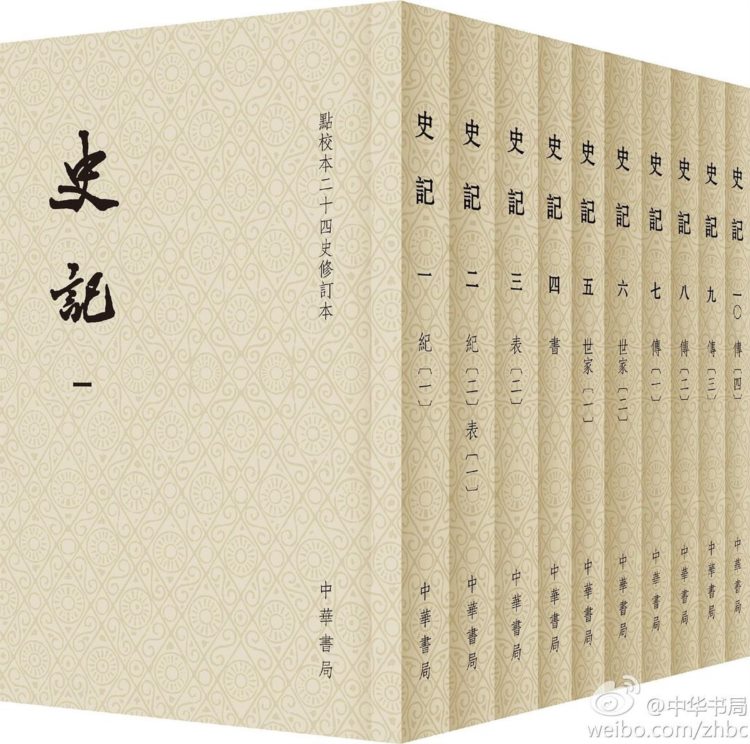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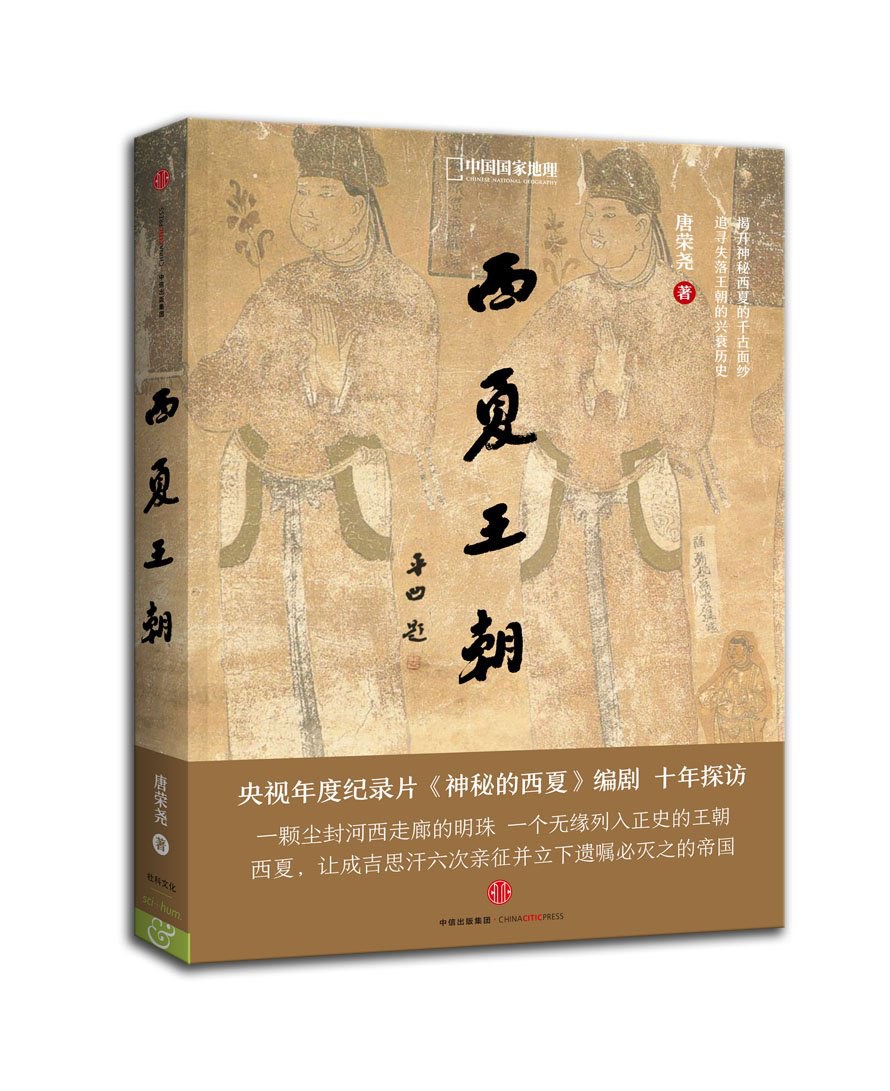
我来回答